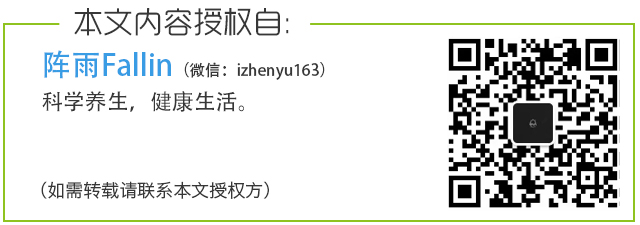现代中国,真的还能指望草药治病么?
11月9日
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,药物研发不但早就达到了分子水平,更是已经可以做到针对基因,从而生产出靶向药这种东西。如果还用尝百草的手段寻找新药,跟现代制药业的效率相比,可以说低得令人发指了。
神农尝百草,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了。这个故事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一点,植物是有药用价值的。
不过有个小问题,神农尝百草,真的是在找药吗?如果是真的,那他为啥不叫“神药氏”?
关于这个问题,清末的大学问家俞樾曾经有过详细论述。
按照俞樾的观点,神农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他的主要功劳当然是在找粮食。要是连粮食都没有,没等得病就先饿死了,药还有什么用?
现如今,世界上大约有60%甚至更多的人仍然直接将植物作为药物。那么,我们现在还能不能把植物当成药物使用呢?
曾经,植物一直扮演着药物的角色
事实上,在漫长的历史里,医生一直把植物当成药物使用。
比如说古埃及,在几千年前就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文明。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,他们的医学相当发达。
考古学家发现过古埃及的医学著作,在其中记载了这样一种药材,就是柳树皮。古埃及的医生发现,柳树皮可以退热,所以就把这玩意让患者服用。
还不止是古埃及人,到了中世纪的英国,一个姓斯通的牧师也这么认为。
当时治疗疟疾用的是金鸡纳树皮,但是这种树皮产量少,所以价格昂贵。于是斯通牧师想找一种更便宜的东西,目的是想替代它。而斯通牧师找到的东西也是柳树皮。
问题是,柳树皮真的有效吗?真的可以退热吗?
答案是肯定的,古埃及的这种药物经得起经验医学的检验,而斯通牧师给患者服用之后,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毋庸置疑的是,植物当然有药用价值的。
那么当医学发展成为现代医学的时候,柳树皮还能坚持住吗?
柳树皮的秘密
柳树皮确实有用,但是它的成分那么复杂,到底哪种东西能起到退热的作用呢?这个问题让科学家们困惑了很久,后来还是化学家们最先有了突破。
先是有人研究一种叫“绣线菊”的植物的时候,发现了一种有机酸,当时也不知道这玩意有啥用,反正就顺手起名叫“绣线菊酸”。
后来其他化学家研究柳树皮,也发现了一种有机酸。再后来,发现这俩是一回事,就统一叫做“水杨酸”。继续研究了一下发现,这个东西在人体里能发挥退热的作用。
原来,柳树皮之所以能退热,就是靠的水杨酸。
到了这个时候,柳树皮已经开始接受科学的洗礼了。它有什么用,为什么有用,逐渐都有了科学的解答。
也就是说,虽然在几千年的时间里,医学知识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但是植物作为药物还是有一席之地。
但是既然这样,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吃柳树皮了呢?因为经过现代科学的洗礼,医生们对药物的认识加深了,他们发现了更好的方法,也就是使用植物里的有效成分。我们还用柳树皮当例子好了。
水杨酸的新生
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,柳树皮里有水杨酸,这东西可以退热。
所以很容易想到,如果把水杨酸提取以后,直接当药吃,那肯定比吃柳树皮效果好。
大约一百年前,医生们确实是这么想的。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,水杨酸实在是太难吃了一般人根本接受不了那股味。
于是,一家德国公司开始研究这个问题。这个时候,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了水杨酸的分子结构。
于是,他们在水杨酸的分子上加了个乙酰基,就让它变成了乙酰水杨酸,而且这家公司还给乙酰水杨酸起了一个新名字,也就是咱们都非常熟悉的“阿司匹林”。
拜耳公司的负责人卡尔·兑斯伯格,在他的干预下乙酰水杨酸完成了全面的临床试验
到这里,我们就更加清楚了,植物有药用价值不假。
但是,在古代是靠医生的经验,在无数的患者身上试出来的,而且就算是有用,其实医生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有用。
在现代医学里,对于植物提取药物这件事,已经认识到了分子的层面,到底什么有效,说得清清楚楚。
那么,当你发烧的时候,有两个医生给你治疗方案。
一个让你把柳树皮烘干、磨粉,然后冲水喝,而另一个医生给了一盒阿司匹林,你会选哪个?
事实上,搞懂了这个问题,不仅仅是治疗发烧的问题,而对认识整个医学体系都有帮助。
知道了这些,是不是可以理解为:植物里有药用价值,所以哪怕是医学进步到了今天,植物还是不可缺少的一环?咱们继续看
阿司匹林的故事
阿司匹林的发现虽然跟柳树皮有关系,但是,真正生产它的时候,根本就没用柳树皮。
因为一旦知道了有效成分是什么,科学家们就能找到能好的合成方法。比如说阿司匹林,就可以用苯酚来合成,而苯酚是从煤焦油里提取出来的。
有意思的是,苯酚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来做炸药。结果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,各个国家都把苯酚当成了战略物资,限制了它的买卖。
这么一来,药厂想要生产阿司匹林就没了原料。幸亏在这个时候,大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,而生产唱片也需要苯酚。
爱迪生没有足够的苯酚怎么办?他马上发明了新的合成苯酚的方法,还自己开了俩工厂,每天能生产6吨苯酚,不但自己足够用了,还能剩下来一半卖给药厂。
在这个有趣的故事里,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。原来,阿司匹林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柳树皮的束缚。
也就是说,虽然水杨酸是在植物里发现的,但是它的工业化生产跟植物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这就是植物药物经过现代医学洗礼之后的样子。
但是,看完了这样的故事,我们是不是想到,在未来的药物研发过程里,是不是吸取阿司匹林的经验,继续在植物里寻找有用成分,然后再研究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呢?
我们还需要“神农”吗?
想要明白这个问题,我们还要回到斯通牧师的故事里。
为什么他能想到柳树皮有药用价值呢?是因为在当时,医学界信奉“瘴气理论”,也就是说当空气被污染的时候,就会引起传染病的发生。
所以在烟雾弥漫的水边,往往就是瘟疫的源头。
除了这个理论,还有一个“信号学说”,是说在引起疾病的因素的附近,一般就有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。
所以,斯通牧师认为,水边的空气污浊,会导致瘟疫,瘟疫会让人发热,那么水边的柳树能治疗发热。
很明显,他所依据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。
我们今天见到的几乎所有源自于植物的药物,都经过了类似的过程。
先是在漫长的年月里,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被发现,然后又经过了科学长时间的检验,最终发现了有效成分,并且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手段。
但是!
根据我们现在的药物研发水平,还需要科研人员按照斯通牧师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自然界吗?
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,药物研发不但早就达到了分子水平,更是已经可以做到针对基因,从而生产出靶向药这种东西。
从研究药物起效的分子机制作为起点,采取化学合成的方法制造新的药物,这样的效率当然会更高。
如果还用尝百草的手段寻找新药,跟现代制药业的效率相比,可以说低得令人发指了。
图片来源:图虫创意